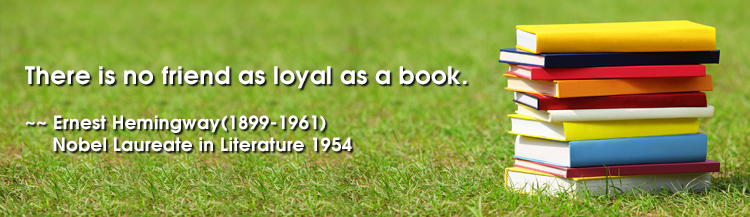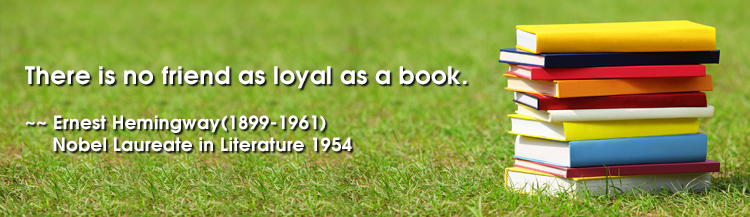七月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,一位身穿黑衣,文質彬彬的男士參觀了傳理視藝大樓。他說:「已有好一段日子沒有回來傳理學院了。」他是誰?他是傳理學院校友、電影《風暴》的導演袁錦麟。他將與大家分享當編劇和拍攝電影的心路歷程和他最愛的電影。
記者:你在浸大修讀電影時,是個怎樣的學生?
袁:還記得浸大傳理系的傳統是,師弟妹協助師兄姊,通力合作,什麼都一起做。我在修讀電影時,從一年級起,已經是「做牛做馬,服務大眾」(說笑),主要是幫忙攝影,同時間兼顧三、四個項目是等閒事。其實,與師兄師妹一起做習作是很好玩的,我們經常捱更抵夜,帶備睡袋在當時的301號房留守。
記者:為何醉心電影及電影工作?
袁:我讀中學時是戲劇學會幹事,又是攝影學會副主席,再加上有位中學師兄回母校介紹過,所以選擇入傳理學院好像是順理成章的。畢業後,做過短暫的助攝工作,後來當過副導演,製片。也曾在徐克導演的新視覺特技工作室當經理,開始認識特技。執導廣告片不久,便受邀在有線電視外判項目中自編自導了《愛情加油站》。這部電視電影獲得張艾嘉導演垂青 ,邀請我將之拍成電影。但我不想重複自己,於是她改為找我寫劇本,當中一部就是與她聯合編導的《想飛》。
記者:你是否對寫和拍警匪片情有獨鍾?
袁:這其實是一個機緣變成的美麗誤會。無可否認,我編寫拍攝了多部警匪動作電影。但從寫作的角度看,動作只是包裝,內容才最重要。當然,你要知道如何掌握你所寫的類型,因為在商業范疇下,觀眾要知道他們應該有什麼期望。
記者:你最近所拍的電影《風暴》想帶出什麼信息?
袁:《風暴》想質疑人性的本質、善惡的界定。一瞬間的決定,可使一個所謂好入捲入萬劫不復的深淵。同樣,所謂壞人反過來也可獲取另一個結局。那人一生定論是如何,以致何時去劃界?
最初《風暴》是以兩段愛情帶出人性抉擇。後來,因商業考慮,老闆決定把一條愛情線連根拔起,另一條削半,同時增加了大量的動作場面。結果換來3.15億人民幣的內地票房和2,500萬的香港票房,對公司來說是成功的。對我來說,《風暴》是一個習作,它給我贏得一個掌控大製作的經驗和另一個起步的平台。
記者:一個導演和編劇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?
袁:初出茅蘆時,掌握不到自己的時間,因為我無法控制何時下班,約朋友吃飯。當導演時,能掌握的時間較多,但同時壓力也更大。各個部門、每個細節都等著導演去做決定,每部電影的成果都影響你在行內的發展。其實,我用於編劇的時間比我做導演的時間長。我喜歡把鏡頭、燈光和聲音都寫進劇本,所以作為又編又導的導演,電影已在腦海中拍過很多次,但現實中,外來的干預很影響最後的面貌。
作為編劇,我做的事情跟普通人一樣,因為要窺探生活,才可以寫出實在感。作為導演,拍攝都是廢寢忘餐的。現在電影的製作費很大,數千萬以至上億元的製作比比皆是,導演要為所花的每分每毫負責。權力越大,責任越大,當導演要有承受得起戲裡戲外壓力的準備,但這一切也是應該的。
記者:你是如何創作劇本的呢?最喜歡在那裡寫劇本?
袁:靈感是遙不可及的。所以閒時會多留意新聞、看小說、看電影、看話劇及舞蹈、聽音樂等等,注意生活上人事物的細節,有時需要筆錄下來,儲備一下。開會以外,我喜歡泡在家寫作。當你好像看到自己筆下人物的一言一行在你眼前播放,當感覺筆停不下來時,你便知道自己走對了方向。
記者:你下一部電影以什麼為主題?
袁:正在編寫自己下一部導演作品,但最快面世的電影應該是我監製和故事編劇的《捉妖記》,已經進入後期工作,導演是《史力加3》的導演許誠毅,這是一部結合動畫和人的合家歡電影,也是華語電影少涉足的嘗試。對大部份人而言,妖怪是可怕的。但我創造的妖,其實只是人類罕見的另類生物,是人的恐懼和無知,令其魔鬼化。我覺得現在人與其他生物越來越難共存,希望能透過此老少咸宜的電影提醒下一代,要懂得尊重生命和大自然,也希望他們有這種使命感。
記者:請分享你最喜歡的一套電影和一個導演?
袁:一個電影人可能有很多部喜歡的電影。而我最尊重那些能夠持續拍出好作品的導演如老牌的黑澤明,新的有墨西哥導演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。我喜歡他至今所拍的所有長片,包括《狗男女的愛》、《21克—生命可以有多重》、《巴別塔》和《最後的美麗》。以《21克—生命可以有多重》為例,導演以人離世一刻消失的21克帶出靈魂的重量,這21克分佈在全片的124分鐘之內。
受訪者檔案:
袁錦麟校友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,身兼編劇和導演,亦擔任電影策劃及監製等工作。他最近導演的《風暴》在香港和內地錄得驕人票房成績。
|
|
 |
 |
 |
| 袁錦麟校友參觀電影學院 |
| |
| |
 |
 |
| 袁校友參觀傳理學院並與電影學院總監葉月瑜教授(左)會面 |
| |
|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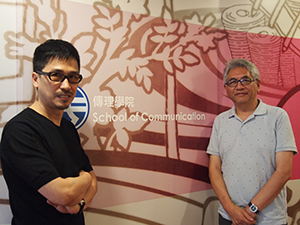 |
 |
| 電影學院副總監及首席講師文樹森先生(右)與袁校友暢談 |
|